Copyright © 中国民间人才网 京ICP备2023017440号


吴生泉 (四川)


“人死如灯灭。”这是祖母常说的话。
或许,这句话源于某位老人的离世——或是她轻声安慰他人,劝慰生者节哀顺变;或是她独自呢喃,宽慰自己:生死自有天命,人终有一别,须得坦然。而今,说这话的祖母早已作古,那盏曾照亮我们童年的煤油灯,也早已悄然熄灭。是啊,人生如灯,明灭有时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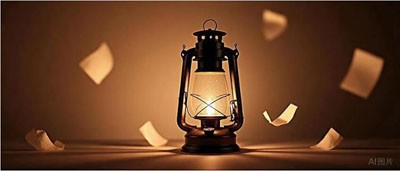
记得那时,家里的灯是煤油灯,弱不禁风,却曾在时光深处摇曳,镀亮过我们的童年。
祖母曾出过一个谜语:“指头大一个宝,满屋子装不了。”我们猜了又猜,始终不得其解。那时家里太穷,吃的在肚里,穿的在身上,除了几间茅草屋,几乎一无所有,哪还有什么宝贝?后来,在灯焰忽明忽暗的提示下,我们终于猜到了——灯,谜底是灯!是啊,它仅有指头大小的火苗,却能将满屋子都照亮,甚至从木门的缝隙、牛肋巴窗户漏出几缕微光。在那个不知电灯为何物的年代,在黑黢黢的夜晚,那盏煤油灯,便是最珍贵的宝贝。
那时,灯光昏黄,可我们的视力却出奇的好。兄弟们挤在灯下写字、做算术,或是捧着小人书看得入迷,甚至在灯光与墙壁之间玩起手影游戏来。特别是低头写字时,由于太过专注,头发常常被灯焰燎着,“嗤——”的一声,等闻到一股焦糊味才会惊觉。那情形,跟飞蛾扑火似的,至今仍记忆犹新。
煤油灯像极了“弱势群体”——挪动灯盏时,须小心翼翼:一手拿灯,一手挡风,生怕给吹熄了。最怕夜风突然造访,若是忘了插门栓,灯便瞬间熄灭,我们便会陷入无边的黑暗。“打黑摸”是当时最尴尬却又难免的事。那时候的黑夜真黑啊,伸手不见五指,抬头不见月华,比课文里形容的“黑暗的旧中国”还要黑上几分。更要命的是,听过不少鬼故事的我们最怕那些鬼怪跟随那妖风混进屋子里,往往吓得往祖母身边凑。
可祖母是不需要灯的。灯的或明或灭,对她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。她能摸黑抹苞谷,摸黑砍猪草,摸黑喂磨……不是因为煤油金贵舍不得点灯,而是双目失明的她,早已习惯在无边的黑暗中摸索。或者说,自从被一线麦芒夺去光明后,她早已与黑夜融为一体。灯对她而言,早已失去意义。
但祖母说,她能感觉到灯光的存在。她说,灯就是红红的一团。或许这只是一种心理作用,或许这只是她的自欺欺人,但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她的“心明眼亮”。那时,我们常在夜间推磨,不肯吃闲饭的祖母总是争着喂磨。因不满意祖母用勺尖勾一点点粮食喂磨那种慢吞吞的“慢动作”,我们总是赌气将磨盘拉得飞快,想逼她让位,可她依然不慌不忙地舀料、喂磨,而且总能精准地避开呼啸而过的磨担钩,害得我们有些气急败坏,却又无可奈何。
是的,上帝为某人关上一道门,就会替她打开一扇窗。祖母晚年充当“门卫”,全靠她异常灵敏的听觉。当家人都外出上工或上学后,坐在门槛边的她能察觉周围的一切动静,能听出院子里走过的是谁的脚步,甚至能分辨出是哪家的狗打哈欠的声音。任何风吹草动,都逃不过她的耳朵。
祖母心中仿佛有一盏长明灯。她是整个院子里有名的和事佬,左邻右舍起了纷争,都乐意找她“断道理”。她常说:“别看我是个瞎子,但谁是谁非,我分得清楚,决不说瞎话。”双目失明的祖母,心里比许多明眼人更亮堂。
失明的祖母常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。逢年过节,她给我们分发压岁钱时,总要从头到脚逐一抚摸,不为别的,只想感知孙娃子们、孙女儿又长高了多少,她也用同样的方式了解我们那尚未过门的嫂子,感知一下她未来的孙媳妇到底有多高大、多结实。作为我们的“老祖宗”,她必须做到心中有数——一切尽在“掌握”之中。那时的我们,总因联想起课文中那个“盲人摸象”的故事而忍俊不禁。留在记忆里的那双老手,虽瘦骨嶙峋,却也温柔而温暖。
有人说,人生如灯,要想灯火长明,就得省着油,别把灯芯挑得太高,别把灯光弄得太亮。说这话的是位视力正常的“明眼人”。不必说,相对祖母而言,他的生命只是与时光磨磨蹭蹭的苟延残喘;不必说,不想“加油”的人生,注定黯淡无光,注定死气沉沉。
在人世间行走,便是与“许多灯”打交道。上帝给每个人的灯油都差不多,也很宝贵。只是有的人吝啬,总想成为一盏“省油的灯”;有的人却大方又大气,尽量将自己的灯焰拨得更明更亮些,用自己的光明照亮外界,感染他人,甚至,不惜倾注一部分灯油去照顾他人,温暖他人。
那年,祖母走后,年幼的我们连续几个晚上争着为她“送火”(一种为守灵时添灯油的风俗)。在风中摇曳的灯光里,我们仿佛看见了祖母那温暖的微笑。
是啊,人生如灯。
祖母那盏灯,一直在我们心中亮着,温暖着。
作者简介:吴生泉,四川武胜烈面中学教师,写作爱好者,偏爱散文及散文诗写作,作品散见多家报刊,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,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。




欢迎访问北京智慧子月科技有限公司
热点内容
Hot content
视频推荐
VIDE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