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pyright © 中国民间人才网 京ICP备2023017440号


高永平 (四川绵竹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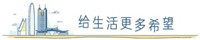

老屋藏在绵竹的大山里,就挨在大路旁。三间青瓦房前是院坝。坝的尽头有两棵杉树,树下蹲着的便是我要说的那口“猪草缸子”。
堂屋居中,进屋便能闻到肉香。右边往上看,两根金柱架着一根粗杆,一个个腊肉挂在杆上,盐霜裹着肉身,随风晃动。右边一间向前搭了个“偏偏”作厨房,门正对阶沿;左边一间挨着的草屋是猪圈和茅厮,圈在里,茅厮在外。
从茅厮正面下阶沿,就是进出的小路,有四五丈远。缸就在路左,紧挨着茅厮;路右是两分田的菜园子,是我家的自留地,周围栽了十来棵杂树。小路尽头便是大路,往右两里地就是那汪闻名川西的大天池。
在这样的老屋里,住着我们一大家子。那时我们一家八口:外婆、父母、舅舅,以及我们四个小辈——我是老大,还有两弟一妹,妹妹是老幺。我们的记忆都是在老屋里长出来的——厨房调料架上总放着猪油罐,还有锅灶前的那口鼎锅。
记得那口鼎锅一直吊在铁链子上,黢黑锅身裹着锅煤子。锅里总存着多半锅水,灶火余温焐着。未开时,细白汽在锅里打转;一滚便呼呼冲起,漫过灶房,顺着檩子、椽子钻向瓦缝,在屋顶凝层薄雾。还有,那鼎锅上面挂着的被水和烟火熏得黑黄发亮、油水欲滴的尿泡肠,尤其是杉树下那口缸,总是挥之不去。
在那不用猪饲料养猪的岁月,平时,就着潲水兑草喂,哪家的猪都不会饿着。但寒冬腊月,冰天雪地,地里的草早被冻成了枯丝,怎么办?外婆和母亲却从不犯愁——她们早有“囤草良策,白露前后择时行动。
记得是在一九七五年白露前的一天,早上雾气特别大,但在九点就全部散尽。中午,外婆对母亲说:“干雾辰时散,要晴九天半”,后面十天都是囤草的好日子,要快!
第二天,母亲拿着割猪草的小镰刀,挨户喊上七八个手脚麻利的阿姨婶婶:“船底窝、青龙嘴,哪里草肥去哪里!”山窝窝里的野草正憋着最后一股子嫩劲:野蒿在疯长,马齿苋、车前草在路旁向她们招着手。一人半天能割几十斤,装背兜时都弓着腰使劲按,装满后再往上码,码成一座小山,随处找几根竹签、树枝插牢别实。小腿上的裤子早被露水全部打湿,巴在腿上却透着欢喜。
下午再去一趟,攥着“7”字形的镰刀在坡上割——弯着腰一勾就是一把,比普通镰刀省劲多了。一天下来,堂屋堆起一人多高的青草山。
“草山”码成圆柱状、用粗实的竹杆插实固定后,砍草的活儿就轮到我父亲了。夜里电灯光下,父亲力气大,拿着磨得雪亮的砍草刀,站在中间单臂挥刀围着草堆砍。每一刀砍下去,草像断了崖似的,随着刀上的反光飞向四周,刀口齐齐整整,空气中满是草的鲜香味。
母亲和那几个阿姨婶子早围着草堆坐成圈,父亲砍下来的草一落地,她们就双手揽过来,拿起砍草刀往细里剁。刀刃起落间,让人眼花的光也跟着闪,细碎的草绿莹莹地堆着,像摆放了一屋子翡翠。
驼背老舅也没闲着,时时递碗凉水让人喝——他因残疾学了理发手艺,家里常摆着理发椅,这会儿便坐在上面,给大家讲些笑话或神话故事。一则刚讲完,有人喊“巴适!再来一个,”满屋子的笑声就没歇过,和着“咔嚓、咔嚓”的剁草声溢出屋外,越过树梢,在屋顶上打了个转转,飘得老远。
然后是最热闹的环节——装缸。杉树下的那口“缸”,其实是父亲亲手造的:早年间他先在地上挖个一人深的大坑,再用石头块和三合土砌成,缸沿高出地面几十公分。父亲左手因工伤从手腕处截了肢,绰号“一把手”,外婆总让我们用热毛巾为父亲擦头和背上的汗。
这口缸能装下三方草,上午在清洗时,父亲把缸壁上蒙着的那层暗绿青苔慢慢启掉。母亲等人用撮箕端着碎草往里倒,父亲脱了鞋,光脚跳进缸里踩,“咚咚”地跺——四周缸壁像被唤醒,回声应和,竟比踩跺声还大,钢响钢响,悦耳动听,好似庆收在擂鼓。
草踩得实实的,该压竹笆了。那是父亲早些日子用略短于缸长的竹杆和篾条扎成的长方形竹笆,扎前他总用右手卡着缸的四周量尺寸。笆子刚好盖满缸口,再压上几块长了青苔的大石头。
最后一步叫浇水封缸。灶上,外婆早烧好开水,用木桶抬着倒进缸里,水汽裹着草香漫上来。水得漫过竹笆子,像给草加个防护罩,隔绝空气与草接触——开水封缸是为杀菌,杀灭虫卵与杂菌,确保囤草来年不生蛆、不变质。
封缸后,日子就静静等着。石缸蹲在树下,像个沉默的老者。过些日子上放学路过,就能闻到股酸溜溜的香,那是草在水里悄悄发酵。缸沿常渗出水珠,顺着青苔往下滴,在地上积成个小水洼,映着天上的云。
入冬后,缸里的草就成了宝贝。掀开竹笆子,黄亮亮的草没等入眼,酸香早已钻进鼻孔。外婆握着磨得发亮的长柄木勺舀出来,木勺沿还沾着去年的草屑。她沥干草里的水分,再和烧开的潲水和匀倒进猪槽,两头黑猪“吭哧吭哧”抢食,尾巴甩得像风车车在转。外婆总说:“这草发过酵,比啥都养膘。”
那是肯定的,囤了缸草的人家,年猪越喂越壮,背脊上的膘能摸出寸把厚;没囤草的,猪瘦得像片瓦,不等大雪封山就宰了,肉炖出来寡淡得很。
外婆的年猪,总要喂到腊月二十几才杀。褪了毛的猪身油光水滑,腌入大盆里做成腊肉,黄亮得很,看着就想咬一口。厨房调料架上的猪油罐,当天就装满新炼化的猪油,白花花的油脂在罐里凝着,罐口还沾着几滴透亮的油星子,凑近了能闻到热猪油冷却后那种温厚的香。
灶头钩子上,刚洗净的猪尿泡也被填得圆鼓鼓的,表面处还挂着几滴水珠,挂在那里晃晃悠悠,像个半透明的小灯笼,等着烟火气慢慢地,把日子的滋味一点点熏腌进去。
杀年猪那是必须要开荤的,外婆从菜园子扯了把带雪蒜苗。五花肉煮熟凉透切薄,下锅煸出油卷成灯盏窝,混着蒜苗一炒,香气直钻鼻腔。这口回锅肉,瘦嫩不腻,吃起来满口生香还有嚼头——全因那缸发酵猪草喂得扎实,巴适得很!
惊蛰前后,缸就空了;可天池雨水多,没多久便积起大半缸清水,水面上慢慢长出绿色的水藻,鲜灵灵的,很是养眼。每到这时,缸边总会围一群放学后的孩子,趴在缸沿上,举着小木棍去戳水里的蝌蚪、小青蛙,看它们一扭一扭地游着,笑声能漫到大路上。
这口缸从一九七六年的春夏之交开始,派上了一些用场。那阵子闹地震,邻里把防震棚搭在路边,父亲看着就直摇头。他决定在缸上动手:铺木板、架人字架,蒙油绸、盖草顶。大雨一来,别家路边的棚子遭了淹,这缸上的棚子倒防了涝。
七月初,我初中毕业。此前两年,学习冒尖,常领头做班务,升学本无悬念。未满十四岁的我,心里揣着热乎盼头。舅舅说“毕业了跟着我学理发吧。”于是,杉树下那口老缸旁,成了我练手艺的地方。先练双手平举,举到胳膊不酸就成;再双手各握一根筷子,仿着握剃头刀的架势,练手腕左右摆,学剃头修面的细活。
七月底,唐山地震消息传到山里,一家人挤在棚里睡。缸下的老酸味虽冲,却睡得踏实。为应急储备干粮,外婆先把玉米炒熟,父母再用手推磨碾成炒面,装在布袋里搁在棚角。弟妹几个嘴馋,常趁大人不在,要么倒碗开水冲成糊糊喝,要么直接抓一把塞嘴里——那干面呛得人直缩脖子。
八月初,推荐上高中的名单下来,没我的名。
母亲不甘心,到处去咨询。找学校,找公社,后来干脆往山外的汉旺镇去,找招生学校。老家到汉旺,往返六十多里地。她每次回来都不多说,只一句“再等等”,那三两个字比山路还沉。
九月的一天,我正在缸边练着那些动作,母亲从外面回来,裤脚上全是灰。她先瞪了舅舅一眼,再对我说:“把书翻出来,多看看,毛主席追悼会过后,去汉旺读高中。”
余震歇了,棚子拆了,白露近了……再看那缸,青苔缝里像还藏着木架吱呀、油绸挡雨的响,还有母亲瞪舅舅时的眼神……
岁月悠悠缸未移,忽逢地动故园离。汶川大地震那年,大天池的人家全部异地安置到了大山外面的平坝地区——汉旺镇,汉旺成了大家的新家。
可每次想起老家,最先冒出来的还是杉树下的那口缸——那口猪草缸子至今还蹲在杉树下。如今的乡亲,能下单网购、可点外卖,动车擦镇而过,家家都住上了楼房。可是,每当想起那口缸,想起老屋里的腊肉香味,想起孩童时踩草的喧闹……想起的不只是画面,还有他们当年骨子里的那股精气神——外婆的生计、母亲的干练、父亲的实诚、老舅的热情,都没随着时光散掉,反成了我心里一直的标杆。平日里干活、想问题、待人接物时,总不自觉照着他们的样子往下走。
他们在船底窝割草,灶前烧火映脸红,竹篾影里低头忙,堂屋里的说笑像说书,缸旁我们给父亲擦背……日子藏在老屋脊下,有笑有累有烟火,它像那口缸,默不作声却扎实。
如今再想,当年那缸里被石头压着的,哪里只是猪草?分明是老秤也称不出好孬的日子。
去年冬天,大天池接连下了几场雪,那口缸又被大雪封缸。蹲在树下的它,孤零零的,像替走了的人,仍在等我们回去看看。
如今的大天池,除了乡亲们的新生活,还迎来了新机遇。近期,大天池来了一批新人,当地规划在那里要建冰雪小镇,眼下正拓着路——在老路基础上改扩建,从山下往山里修。
那口缸终于可以再次派上用场。虽然它仍然在树下蹲着,至少能候着那一天,为大山里的旧时光与新奇迹,作个见证。
或许未来,石缸终被覆土,但当年“缸藏”的故事,一定会一直讲下去。就像那口缸,虽可能消失,却早把岁月的味道刻进了心里。
【作者简介:高永平,德阳绵竹人,中学高级教师,退休后为绵竹市门球协会及绵竹市老科协会员。】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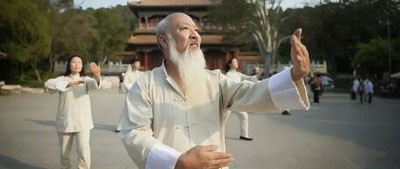


欢迎访问北京智慧子月科技有限公司
热点内容
Hot content
视频推荐
VIDE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