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pyright © 中国民间人才网 京ICP备2023017440号


廖正英(河北祖籍四川武胜)


“人固有一死”,这声从生命深渊传来的回响,既是冰冷的铁律,亦是灼热的启蒙。它如一把锋利的刻刀,悬于每个清醒灵魂的额前,迫使我们剥落浮华,直面存在的本质。正是在这无可遁逃的终局映照下,生命之光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光谱——或如风中残烛般黯淡飘摇,或如经天彗星般璀璨永恒。
对死亡的确知,非为引人沉沦于寂灭的寒潭,而是为唤醒生命最本真的激情与尊严。海德格尔以“向死而生”的哲思,为我们劈开一扇透光的窗。唯有当“死”的阴影清晰地投射于“生”的幕布之上,我们才能从日常的沉沦中惊醒,开始审视“我为何而活”这一终极命题。太史公忍辱负重,在生死抉择的峭壁上,毅然选择“重于泰山”的崎岖之路,以血泪浇铸成不朽的《史记》。他之生,因对终结的深刻凝视而获得了骇人的密度与韧性。死亡这面无情的镜,就这样逼迫我们为短暂的存在勾勒轮廓、赋予意义,从蒙昧的“活着”跃升至清醒的“存在”。
当生命意识的火炬被点燃,前路便展现出不同的轨迹。一种活法,是在死神阴影下的匍匐与攫取。他们或是被“终有一死”的恐惧所奴役,在感官的饕餮与物质的迷狂中寻求片刻的麻痹,如《项链》中的玛蒂尔德,为一夜虚荣付上十年艰辛;或是在“死即虚无”的叹息中,陷入“何不秉烛游”的及时行乐,其生如浮萍,随波逐流,未曾激起一丝精神的涟漪。另一种活法,则是将死亡铸成丈量生命价值的尺度,以创造对抗消亡。他们如精卫填海,以有限之躯,追求无限之价值。杜甫身历离乱,穷愁潦倒,却将一己之悲悯化为“安得广厦千万间”的千古绝唱;苏格拉底在毒酒面前,从容论道,以生命祭奠真理与律法的尊严。他们的存在,因自觉背负死亡的重量而愈发浑厚,因投向永恒的价值追求而超越了生理生命的限域。
于是,我们窥见了生命最为壮丽的悖论:正是死亡的必然性,为生命意义的绽放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,也为生命价值的高下之分立下了最终的界碑。孔子临川而叹“逝者如斯”,却从中淬炼出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担当;王羲之在兰亭雅集中感怀“修短随化,终期于尽”,反而激发出对“后之视今,亦犹今之视昔”的深沉历史关怀,让笔墨文章穿越时空。那些伟大的灵魂,正是在确认了舞台的短暂与必谢之后,反而能全情投入,将这场演出演绎得淋漓尽致。他们以思想、艺术、仁爱、壮举,在历史的长河中投下巨大的身影,实现了精神的赓续。臧克家先生为纪念鲁迅而作的诗句,或可作为一种形象的注脚:“有的人活着,他已经死了;有的人死了,他还活着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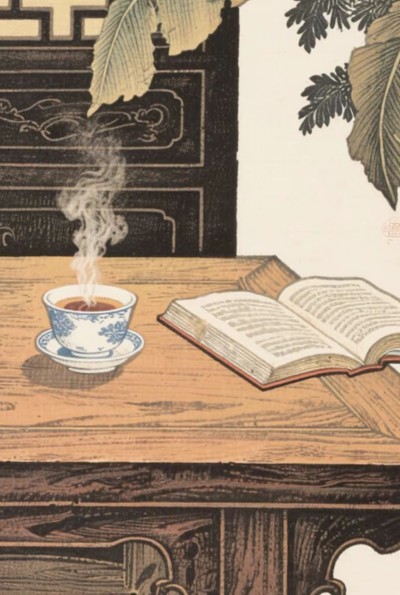
死亡,这生命的铁锚,既是一切意义的终结者,也可能是一切意义的奠基者。当我们不再回避那终将到来的黑夜,反而能以澄明之心凝视它时,每一个白昼便被赋予了全新的光辉与质感。愿我们都能在“向死而生”的智慧烛照下,审慎抉择各自的存在方式,让有限的生命,在追求真、善、美的无限征程中,敲打出不属于永恒却胜似永恒的金石之音。



欢迎访问北京智慧子月科技有限公司
热点内容
Hot content
视频推荐
VIDEOS